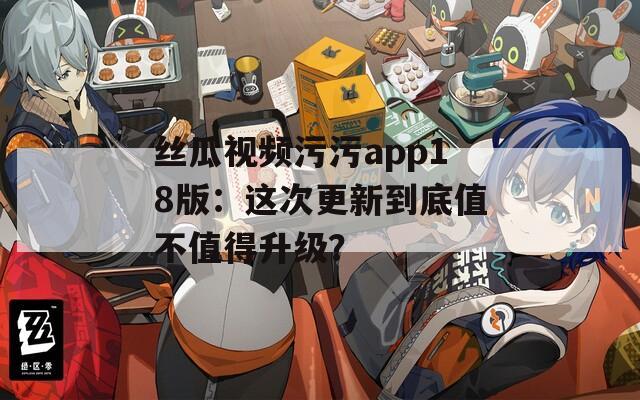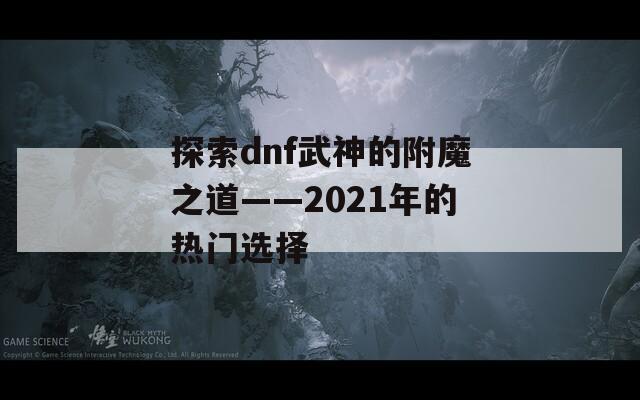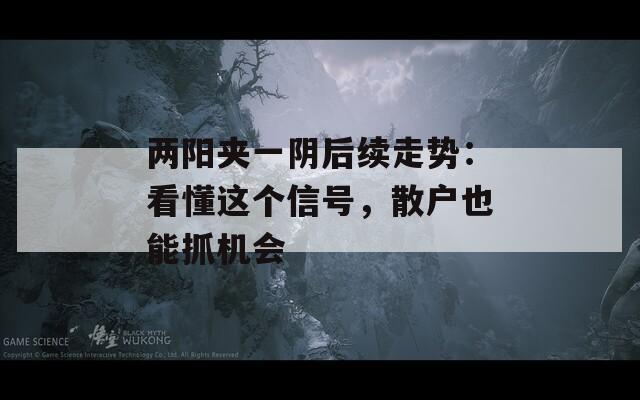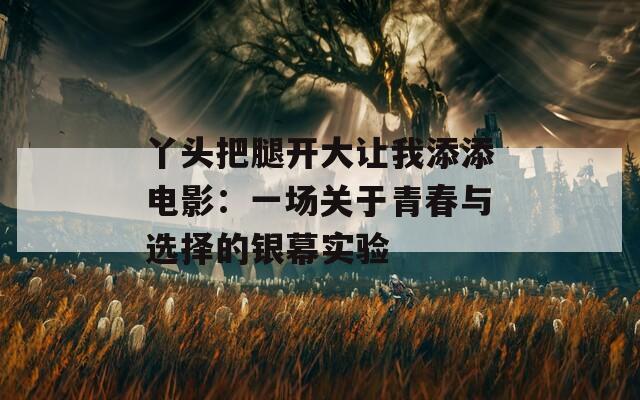锄头下的春夏秋冬
清晨五点,天边刚泛起鱼肚白,**儿子**王建军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走。六亩旱田像块打满补丁的粗布,歪歪扭扭地铺在山坡上。他熟练地弯腰除草,后脖颈的汗珠顺着晒成古铜色的皮肤滚落,在干涸的泥地上砸出硬币大小的湿痕。
十年前从建筑工地回来接手的这片地,土质硬得像掺了水泥。母亲总念叨:"你爹临走前攥着麦穗说,这地养活了咱家四代人。"现在七十八岁的老太太每天拄着拐棍来地头,看儿子把板结的土块敲碎,混进发酵好的猪粪,就像在看慢镜头播放的奇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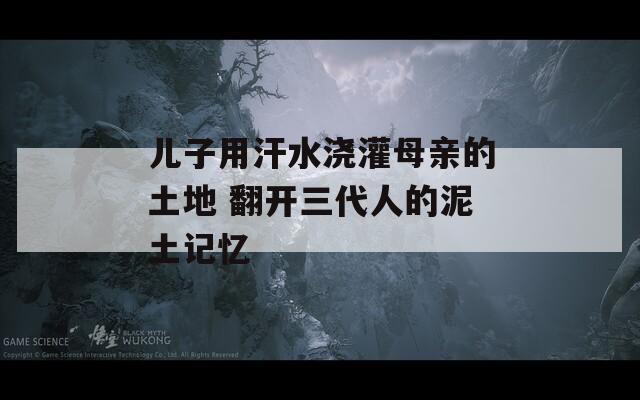
藏在泥土里的账本
村里会计老张扒拉着算盘给建军算过账:种玉米每亩净赚不到三百,打工每天能挣两百。建军却把旧算盘往桌上一拍:"照您这么算,我妈晒的柿饼、腌的酸菜、喂的土鸡都不该存在。"
他在地垄间套种黄豆和南瓜,藤蔓交缠着往上窜。母亲挎着竹篮摘豆角时,常被突然蹦出来的野兔吓一跳。秋收时金黄的玉米棒子堆满院墙,老太太坐在藤椅里剥玉米粒,指甲缝里嵌着的碎屑在阳光下闪着微光。
播种机碾过的乡愁
隔壁老李家儿子买了台红色播种机,突突的轰鸣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。建军依然用牛耕地,黄牛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,摇出的声响和三十年前父亲赶牛时一模一样。有次播种机卡在田埂,倒是建军牵着牛去帮忙拖出来的。
"机器撒种快是快,可种地又不是赛跑。"母亲把浸好的种子装进建军缝补过三次的帆布袋,布袋内侧还留着父亲用蓝墨水写的"庚申年谷雨"。那些被播种机翻出来的碎瓷片,建军都捡回来拼成了半只腌菜坛——正是他爷爷那辈用过的物件。
土地上的传承密码
去年暴雨冲垮西边坡地,建军带着媳妇连夜挖排水沟。老太太急得非要拄着拐棍去帮忙,结果摔在院门口。建军背母亲去卫生所的路上,老人伏在儿子汗湿的背上呢喃:"地养人,人养地,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理儿。"
如今村里年轻人都在县城买了房,建军却把旧瓦房翻新成青砖房。堂屋墙上挂着全家福,相框下方钉着三袋不同年份的麦种。五岁的小孙子在地头追蝴蝶时,建军会往他口袋里塞把带壳花生:"去,给太奶奶剥着吃。"
傍晚炊烟升起时,老太太坐在新打的井台边,看儿子把晒好的玉米码成齐整的金字塔。晚风掠过层层叠叠的梯田,带着泥土味的凉意拂过祖孙三代的脸庞。拖拉机的声音渐渐消失在暮色里,牛铃铛的叮当声依旧清脆,像土地在说着只有农人听得懂的情话。